新闻中心
- 老虎机游戏app官网版党纪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
- 老虎机游戏app官网版召开首次新时代学科发展工作会议
- 戴逸:把自己的学术生命与清史事业融为一体
- 讣告 | 沉痛悼念戴逸先生
- 朱浒:关于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几点思考
- 中国共产党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党员大会胜利召开 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委员、纪委委员
- 老虎机游戏app官网版党委第三巡视组向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党委反馈巡视情况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牢记领袖嘱托·青春奋进今朝”主题联学活动顺利举办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讨会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总结2023年度工作
- 我校历史学科五项成果入选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拟奖励名单
- 老虎机游戏app官网版人事人才制度改革文件宣讲会召开
- 老虎机游戏app官网版新时代组织工作会议召开 深化学校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系统性改革
- 老虎机官网多项重大重点课题成功立项
- 老虎机官网两项成果入选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拟授奖成果公示名单
- 世界史学位授权点评估会顺利举行
- 《唐宋历史评论》入选为CSSCI(2023—2024)收录集刊
-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 “唐宋史研究的新时代”学术会议成功举办
- 会议报道—中国历史学科自主体系建设规划调研座谈会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参加第六十届田径运动会,取得可喜成绩
- 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 我校两项目入选央视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85周年校庆分论坛“学术期刊与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顺利举行
- 老虎机游戏app官网版第四届“绎思”史学论坛成功举办
- 教育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老虎机游戏app官网版时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老虎机游戏app官网版召开
- “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老虎机游戏app官网版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起师生热烈反响
- 老虎机游戏app官网版召开全校干部师生大会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老虎机游戏app官网版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赴北京十一学校开展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宣布学院领导班子任免决定
- 戴逸丨治史入门:我的学术生涯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考古文博系师生前往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走访座谈
- 一起向未来|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召开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志愿者行前座谈会暨出征仪式
- 2021年度科研与智库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召开,老虎机官网荣获多项表彰
- 黄兴涛译著《中国人的精神》入选2021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人文类)”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举办魏坚教授荣休座谈会
- “第四届北京南海子文云论坛”召开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辩论队荣获老虎机游戏app官网版 第二十九届辩论赛亚军
- [光明日报]戴逸与清史纂修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举办“历史的星空”新生开学第一课系列讲座
- 学习全会精神,把握历史脉搏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党委召开“解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
- 老虎机官网世界史专业本科生在第二届“海国图志奖”评选中再创佳绩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举行2020-2021学年班长述职评议会暨先进班集体推荐评审会
- 历史与政治实验班开班仪式顺利举行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举行2020级本科师生见面会
- 雄关漫道,征途新辟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举行2021级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大会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举行2021级新生开学典礼
- 舞咏而归—中国人民大在职研究生吉家庄考古实习纪实
- 老虎机官网吴欣璇同学获第23届“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全国一等奖、最佳辩手奖
- 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2020届校友返校参加专场学位授予仪式和学院返校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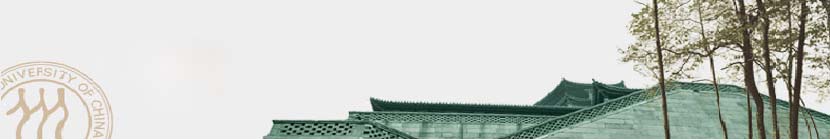
[光明日报]王大庆: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竞争观念比较


王大庆 1969年生。老虎机游戏在线玩平台历史学系主任。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史和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著有《本与末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经济思想比较研究》,译有《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等。

(大英博物馆展出的“掷铁饼者”(罗马副本)藏品(2012伦敦奥运会期间)。)

(小篆中的“竞”和“争”)

(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射礼(复原图))
古代希腊,发展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且较为完备的“赛会制度”;古代中国,虽然没有产生类似的“赛会制度”,但仍存在各种比赛。
那么,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竞争的,他们的竞争观念有哪些异同?这就是本次要讨论的内容。
agon与“争”:古希腊文和古汉语对竞争的不同表述
荷兰学者赫伊津哈曾从“游戏”的角度,把古希腊充满了“游戏精神”的“赛会制度”“赛会精神”视为古希腊人最伟大的创造,而且他还考察了包括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古代文明中的比赛活动,提出了竞赛活动绝不仅仅为希腊人所独有,而是一种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活动的看法。
赫伊津哈提出,在古希腊文中,与汉语中的“争”大体上相对应的字,就是希腊人所谓的“agon”。agon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在现代英文中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汇,从其本身的含义可以大致翻译成contest(竞赛)或compete(竞争),从其字源来看,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指人群的聚集和集中(即“会”),第二是进行某种比赛活动(即“赛”),其中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
因此,我个人认为,agon可以译作“赛会”。起初,agon仅仅用来指称所有的比赛活动,尤其是体育比赛,后来则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泛指所有带有对抗性质或比赛性质的活动。尽管如此,agon始终都没有脱离“比赛”的基本含义,因为上述的所有比赛或者带有比赛性质的活动都有其本身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普遍存在以及游戏者们对这些规则的认可和遵守,成为比赛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古希腊人不仅热衷于各种形式的竞赛,而且还使之社会化和制度化,“赛会制度”及其所蕴含的“赛会精神”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希腊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而在汉语中,用来表达竞争或竞赛的字主要是“争”“竞”和“赛”,其中最为常用的字就是“争”。在《汉语大字典》中,“争”字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争夺”“夺取”,这也是“争”字最初的和最重要的含义。在甲骨文中,“争”字作以手取物状,《说文》:“争,引也”,段玉裁注:“凡言争者,皆谓引之使归于己”,徐灏笺:“争之本义为两手争一物。”由这种“争夺”的本义又产生出其他的几个含义:一个是争斗,较量,《诗·大雅·江汉》:“时糜有争,王心载宁”,陆德明释文:“争,争斗之争。”另一个是辩讼,辩论,《玉篇》:“争,讼也”,《正字通·爪部》:“争,辩也”,《庄子·齐物论》:“有分有辩,有競有争”,郭象注:“并逐曰競,对辩曰争。”还有一个是竞争,《广韵·耕韵》:“争,竞也”,《书·大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可见,“争夺”和“竞争”构成了“争”字的两个基本含义,其中,“争夺”为本义,“竞争”为引申义。
我们把古代汉语的“争”与古希腊文的agon做比较,虽然二者都带有“竞赛”和“争斗”的含义,但在含义上却有不同的偏向和发展路径。在汉语中,“争”字的本义“争夺”有明显的情感色彩,“争夺一己之私利”的负面含义显然是其本义之一,我国古代相应的“不争”思想观念正是由此发展而来。而在古希腊文中,agon的本义“竞争”的含义则较为中性和正面,成为一切有规则的比赛或者带有竞赛性质的活动的泛称,在含义上与汉字“争”的引申义“竞争”的意思更接近。
“竞”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作两人追逐竞技状,上部为辛,是奴隶的标志。《说文》:“競,强语也。一曰逐也。从誩,从二人。”所以,其首要的含义就是角逐,比赛。《说文·誩部》:“競,逐也”。《诗·大雅·桑柔》:“君子实维,秉心无競”,朱熹注:“競,争”。《庄子·齐物论》:“有競有争”,郭象注:“并逐曰竞,对辩曰争。”此外,与“争”相仿,“竞”字本身也有“争辩”的意思。《说文·誩部》:“競,强语也”,段玉裁注:“强语谓相争”。另外,“竞”字还有“强”“盛”的含义,可以视为其引申义。应该说,从含义上看,虽然“争”和“竞”在语义上十分接近,且有重叠,但“竞”字的含义更为中性和单一,含义上与希腊文中表达“竞赛”的agon一词更接近,其本身的含义与现代语言的“竞争”一词大体相当。与上面两个字相比,“赛”字不太常用,且更晚出现。从字义上看,“赛”与“竞”较为接近。
通过考察汉语中用来指称竞争或比赛的这些字,我们可以认为,古代的中国人不仅已经开始有了带有竞赛性质的社会活动,而且,对这些活动背后所蕴藏的一种重要而且普遍的社会现象,即对“争”本身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准确的归纳,因此,这些字本身就透露出了古代中国人对竞争的基本看法。那就是,所有的竞争都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值得关注。第一,“争”的最重要目标就是为了得到某种“物”,既可以是精神上的荣耀,也可以是物质上的好处,在这一点上,与古代希腊人的竞争观念不乏相通之处,在希腊人看来,比赛正是为了获得某种奖励,现代英文中的“运动员”(athlete)和“体育运动”(athletics)等词汇即来自于古希腊文,古希腊文中“运动员”(athlothetes)一词的原意就是“为了获得某种奖品(athlon)而参加比赛的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两个字的差别,“争”在汉语中从一开始具有“争夺”的含义,古代的中国人认识到,世间一切的冲突和动乱都来自于对包括金钱、权力、美色和荣誉的争夺,即对“一己之私利”的争夺,或曰“小人之争”,因此,古人赋予“争”字本身的负面和消极含义十分强烈,而这种情感色彩和价值导向则是希腊文的agon所少有的。第二,在汉语中,用来表达有规则的和有序的竞赛或竞争的词是“竞”“赛”等字,与古希腊文的agon在含义上更为契合,当然,“争”字本身也有这种较为正面和中性的含义,应该说,“争”字这个维度上的含义与希腊文的agon也是比较接近的,符合礼仪规范和道德准则的“君子之争”中的“争”基本上就采纳了这个含义。
我认为,赫伊津哈只看到了中文的“争”和希腊文agon的相似和相通之处,而忽视了两者之间在词义上的差别以及情感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同侧重。只有在弄清了这种“同中之异”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古代中国发展出来的“争”与“让”思想观念有明确的理解。
古代中国的“不争”与“崇让”思想
针对“争”,春秋战国时代的各主要学派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不争”的思想。一方面,在个人层面上,把“不争”看作是一种美德、一种值得推崇的处世哲学;另一方面,从社会制度设计角度,如何息“争”或消除“争”的负面影响也成为当时学者及统治者考虑的问题。
其中,《老子》中关于“不争”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老子的《道德经》中的最后一句话提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遇到冲突时主动退让,不争先,不争强,所谓“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在老子的思想中,“不争”和“无为”是互为表里的,“不争”并不是一味地消极退让,而是不妄为,不强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争而善胜”的目标,“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也就是说,“不争”实际上是一种高级形式的“争”,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乃至于获胜仍旧是最终的目标,即“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在老子看来,所谓“不争”,绝非退出竞争,而是在竞争和进取的过程中处于谦卑的位置,不能只顾一己之私利的强争,而是应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最终取得胜利。
与老子相仿,孔子也始终把“争”视为人们对一己之私利的无度追求,认为它是导致一切冲突、仇恨和社会动乱的祸根。他在《论语·里仁》中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为此,他提出以“义”制“利”,要求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儒家认为,为了平息或消除对一己之私利的争夺,必须要建立起完备而合理的等级制度,以此作为分配社会利益和荣誉的标准,要求人们各安其位,各获其利。
对此,荀子有着更为系统和完备的思考,一方面他把社会动乱的根源直指无度和无序的私利之“争”,另一方面则开出了以“礼”息“争”的药方,甚至认为“礼”的起源正是为了节制人们的欲望,防止人们的争斗。荀子所谓的“争则乱,乱则穷”可以说是先秦各派思想家的共识,也对中国后来的治国理念和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韩非子则敏锐地看到了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的“争”,而且,他还认识到不同时代的“争”有着不同的特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这里,“竞”“逐”和“争”是同义语。他还指出,人口的增长和耕地与财货的紧张及不足是当今“民争”的主要原因。为此,法家提出了“耕战”的治国理念,主张用“法”“术”和“势”钳制和消除这些恶性的“争”。与儒家提倡有等差的仁爱和礼制不同的是,墨家则主张用没有等差的“兼爱”来息“争”。
由此,我们看到,先秦各家学派均把“争”视为对一己之私利的争夺,并认为这样的“争”正是社会冲突与动乱的祸根,只不过在用以消除或缓解“争”的手段和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如果说老子的“不争”思想指出了一条相对消极的进取之路,那么,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主张用“仁”“义”“礼”等较为积极的伦理和道德手段去制约甚至消除恶性的“争”所带来的危害,明确提出了作为“争”的对立面且更为积极的美德 “让”,用“让”来消解“争”。
对儒家而言,崇“让”就是为了隆“礼”,或者说,“让”德实际上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据《论语·先进》载,孔子不满意仲由(子路)说话不谦虚的态度,批评他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也就是说,治国要讲求“礼让”。孟子进一步阐发了“礼让”的重要性,把辞让之心看成是礼的萌芽,即“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也说:“让者,礼之实也。”可见,在儒家看来,如果没有“让”德,“礼”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将会徒有其表。由此,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除了“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之外,又加上了“温、良、恭、俭、让”五种君子的美德。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谦让”之外,“辞让”“礼让”“让利”“让位”等说法或做法也被人们广为接受和熟悉,其中无不蕴含着“让”的思想观念。
“让”的美德不仅被运用普通人对私利的争夺上,成为缓解乃至于化解这些“小人之争”的工具,还被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层面。在作为统治者为政之重要借鉴的史书《左传》和《史记》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为国以“让”的思想。在《左传·襄公十三年》中,作者在记述了晋国的将领们纷纷举荐贤能之人而自身“让位”的故事之后,评论说:“让,礼之主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谦让”和“不争”之美德是否盛行,是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志和条件:“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
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史记》继承、发扬甚至在全书中都贯穿了儒家的“礼让为国”的思想,首篇《五帝本纪》讲述五帝之德,多次提及尧舜禹的选贤、考贤以及“禅让”制度,末篇《货殖列传》则讲述利益之争,阐发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此外,司马迁将《礼书》列为八书之首,在《礼书》的序赞中集中阐发了其“以让化争”“以礼导利”的治平之道。当然,司马迁在看到“争利”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并没有否认其正面作用。他认为,争利是社会前进的杠杆,但“争”若无礼仪和道德规范制约,就会导致“乱”的出现甚至秩序崩溃。
应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争”与“让”辩证关系的深入思考既是对先秦各家思想一次很好的总结和会通,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中透露出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是,“争”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既无法消除,也不必逃避,但是,如果“争”失去了“仁”“义”“礼”等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的制约,就会造成“乱”的恶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在总体上对“争”采取负面的或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同时对那些没有“失范”的“争”,是明确认可或肯定的。同样,与对“争”的认识相仿,古人作为“争”的对立面而提倡的“让”的美德,也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在古代中国的思想观念中,不仅要限制“争”,同样要控制“让”。孔子所谓的“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正体现了这一点。又如《礼记·郊特牲》中讲:“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尽其嘉,而无与让也”,也就是说,在祭礼这种场合,若一味谦让,反而有失于礼,故“无与让也”。可见,“让”与“不让”,合“礼”则“让”,不合“礼”则“不让”。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论语·八佾》中孔子所说的那句名言的含义了:“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里讲的射箭比赛既是一种竞技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礼仪表演,不仅要通过比赛决出胜者,这项活动还承担着明礼、正德等教化的功能。正因为这样的“争”,是合乎礼义的,所以不仅被学者们认可,甚至还被视为应该积极提倡。因而,“礼射”之“争”成为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争”的典范和样板。
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竞争观念的异同
我们结合前文中的有关内容,对希腊和中国的竞争观念的异同,做出一些尝试性的归纳。
先说“同”的一面。
首先,不论是古代希腊人还是古代中国人,都认识到了人世间普遍存在的竞争现象,从中提炼出agon和“争”的概念,用来概括这种现象,并对这种现象的本质、意义和影响等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古希腊人把世界上所有的对立、冲突和争斗都归之于无所不在的竞争,认为对立面之间的竞争既是世界起源的原因,也是发展和变化的根源。例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宣称,世间万物都是由斗争而生成。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则更倾向于把社会中的竞争以及是否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些竞争,直至引申为国家“治”与“乱”的依据。
其次,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中国人都认为,竞争现象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在不否认竞争的前提条件下,对于世界上所有的竞争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两者都认为,好的竞争有利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社会的和谐,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坏的竞争则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甚至会导致社会的分裂、动荡。区分竞争的好与坏的标准,就是其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的要求,以此为标准,中国的儒家等思想家们提出了符合“礼”“义”标准的“君子之争”,区别于只顾谋求一己之私利的“小人之争”,古希腊人也一方面崇尚遵守规则和伦理规范的竞赛活动,另一方面对各种竞技活动中破坏规则的现象进行谴责,并给与严厉的惩罚,同时对有悖于身心和谐和健康发展的竞赛也持有保留态度,或加以批判。比如,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提出,包括血腥和残忍的战争在内的竞争是坏的竞争,而各种和平的竞赛活动则是好的竞争。
由此,我们就要说到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竞争观念中的第三个相似之处。与古希腊发展出完备的赛会制度相仿,在古代中国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竞赛活动,对于这些竞赛,中国的古人都把它们归入“君子之争”即好的竞争的类别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射礼”中的射箭比赛。与希腊的赛会活动相仿,在古代中国举办的这些竞赛中,参赛者不仅都要遵守比赛的规则,还要符合礼仪的规范和伦理道德的要求。我们还注意到,在根据比赛规则决出优胜者的同时,希腊和中国的竞赛活动都带有仪式表演和道德教化的功能和意味。与古代中国通过比赛来学习礼仪规范和培育“君子”相仿,古希腊城邦的各种竞赛活动也承担着培育合格公民的重大责任。在古代希腊,体育比赛不仅大多在宗教中心举办,而且始终没有完全脱离祭神活动的语境,体育比赛本身也带有强烈的仪式特征。同样,在古代中国,射箭比赛也是附属于各种礼仪表演活动,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行礼活动。在这一点上,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竞赛活动呈现出十分相似的思路。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两者同样都具有一定的限定性,古代中国有“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古希腊的竞赛活动早期也仅仅局限在有闲暇接受教育的贵族及其子弟的范围内。
当然,我们在认识到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竞争活动和竞争观念中这些相同或相似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众多的相“异”之处。
第一,从总体上来看,古希腊人更倾向于接受、肯定甚至崇尚竞争,尤其是以竞赛为形式的竞争活动成为希腊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由此发展出“赛会制度”和“赛会精神”。与之相比,古代中国思想家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竞争现象则大多持有一种相对负面的甚至否定的看法,把竞争视为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社会动荡的消极因素,因此,一方面发展出独特的“不争”的美德和“崇让”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如何化解和消除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了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重要目标和内容。
可以说,崇尚竞争与提倡“不争”或“让”的美德,成为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竞争观念最重要的不同点。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种不同,并视之为西方和中国在文化传统上的一个差异。例如,梁漱溟先生在对西方人崇尚竞争的传统进行批判的时候指出,毁灭人类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只知相争不知相让的人生态度。
在看到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尚争”与“崇让”之不同倾向的同时,也不能使之绝对化,因为双方的这种差异只是一种偏向而已。古希腊人虽然没有提出“不争”和“让”的观念,但也不乏类似的认识,在其竞赛性质的活动中所大力提倡的遵守规则的理念和道德教化的意识,同样带有“君子之争”的风范和色彩;同样,古代的中国人虽然大力倡导“不争”和“让”的美德,但也十分推崇正当的与合乎礼法的竞争,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所极力反对的,并不是竞争本身,而是反对那些仅仅为了满足其私欲就导致道德败坏和社会失范的“小人之争”。
第二,对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竞争,古希腊人主张运用“法”即各种规则、制度和法律加以规范和制约。而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则更倾向于运用“礼”即各种社会习俗、伦理和道德的手段来进行约束。
对于希腊人来说,就像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比赛活动无所不在那样,凡是有竞赛的地方就有规则的存在。体育比赛有严格和严密的竞赛规则,裁判员在赛场上依据规则来进行判罚,只有如此才能产生出没有任何争议的优胜者。这些活动的背后,如何用好的规则引导竞争,规范竞争,使人向善,使社会更为公正,是古希腊思想家们热衷探讨的话题。
在古代中国,虽然儒家提出的“礼”治和法家提倡的“法”治也有着与古希腊的规则和法律相似的特点,但占据主流的,还是对内在的道德修养的强调,在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看来,内在的自然要求,比外在的强制力量更加重要,对于导致“乱”的无所不在的“争”,以老子代表的道家学派提出了“不争”之德,儒家则明确地提出了崇“让”的思想观念。
二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古希腊重“规则”而古代中国重“道德”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也不是绝对的,仍然只是一种“侧重点的差异”。因为在古代希腊,除了各种规则的制定和遵守之外,也同样重视内在道德的修养和教化,同样,在古代中国,除了道德修养之外,也存在着包括“礼”和“法”在内的各种规则,只不过与古希腊的“法”(规则)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而已。
最后,我们还可以把古希腊人的竞技体育活动和以“射礼”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竞技比赛做一个直接的对比:作为儒家所提倡的六艺之一的“射”艺,被赋予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考察参赛者的道德品质,所谓“射以观德”,比赛的胜负并不是最重要的,正如《礼记·射义》所言:“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射者,所以观盛德也。”与此不同的是,在古希腊的体育比赛中,虽然也带有以祭神为目的的仪式表演的特征,但运动成绩的高低和优劣,始终是决出优胜者的唯一标准。
(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18年06月03日 06版)
原文链接:
[光明日报]王大庆: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竞争观念比较
| 友情链接: |
|
| 快速通道: | 老虎机游戏app官网版 | 人大新闻 | 国际交流处 | 研究生院 | 科研处 | 招生就业处 | 教务处 | 图书馆 | |
